
dosss 看擺 DJ Shadow 有點意難平,說道:『平時大談如何熱愛hip hop熱愛音樂的那班達人都去了那里?』
我想那班「達人」對於 Hip Hop 的可能定義僅止於外表及型像而已。對於他們,Hip Hop 的定義就是穿 ape 的 XXL、用右 45 度微微向上帶 cap 帽、一「秋」 bling bling 頸鏈、再加對 Gravis 或 TK 氏推介的波鞋。Hip Hop 對於他們可能只是用來跳的,跟跳 Jazz、跳巴西戰舞沒有分別,當然更加跟 B-boy 無關。至於 DJ Shadow 是否在玩 Hip Hop、在玩甚麼類型的 Hip Hop、是否在 scratching、又或者當代 graffiti 是來自費城或 NYC 還是九龍城、又或者 break dance 和 MC 有沒有關係、又或者甚麼是 old school,甚麼是 new school。who cares!
其實,我都也只是 Hip Hop 的外行人。不過如要知道多點有關 Hip Hop 的東西,我認為《嘻哈美國》是一本很好的對於美國嘻哈文化了解的入門。如果可以看看《Scratch》這部電影或者應該說是一部關於 scratch 是紀錄片,則效果更佳。
Scratch固名思義,《Scratch》是一部關於 scratch 的電影/紀錄片。開明正宗講 scratch,導演 Doug Pray 找來很多在 Hip Hop 和 scratch 這方面的重量級人馬來細說其詳,有「歷史」人物 Afrika Bambaataa、Jazzy Jay、and Grand Mixer DXT;亦有訪問了當今 Hip Hop 和 scratch 的至尊 DJ Q-bert、DJ Shadow、Mix Master Mike、Cut Chemist,問他們對於 turntabalism 的見解。
Grand Mixer DXT 和 Grand Wizard Theo一眾 DJ 們也不約而同說,1984年 Grand Mixer DXT 和 Herbie Hancock 在 Grammy Adwards 所玩的 Rock-it 就是影響他們進入scratch 的世界啟蒙。 被譽為 The pioneer of the Scratch的 Grand Wizard Theo said 除了說 "I should get a dollar every time someone scratches a record onto another record." 還鄭重地說了很多人對於 Hip Hop 的誤解,他說 "A lot of people get rap and hip hop mixed-up, its two totally different things. when you say rap, you're saying a MC and DJ. When you say Hip Hop, you're saying graffiti, breakdance, DJ, MC, the way you dress, the way you talk, all element into one, and thats hip hop" 哈,我也相信很多人把 hip hop 混淆了。
DJ Q-bert - the king of scratch講 scratch 怎能少得 DJ Q-bert,在《Scratch》內除了可見到他對 scratch 的看法和他精湛的 scratching;更有他那可同時容納四人同時「jam」scratching 的大「廚」房、千幾二千呎的大屋和很多
MARS-1 的收藏品。在《Scratch》的 disc 2,更有 DJ Q-bert 由 baby scratch 開始教你 scratching。
DJ Shadow - the King of Digging眾所周知 DJ Shadow 的 sampling 與眾不同,皆因他一天到晚躲在唱片店 digging。所謂寶物尋歸底,唱片店老板見他日來夜來,終於開放了很少讓「外人」進入的地庫給 DJ Shadow,要知道這個地庫儲藏了數以十萬的唱片!而且"most of them are nearly untouch" 在《Scratch》內,DJ Shadow 就坐在這個地庫,坐在這個十多萬張唱片傍如數家珍,說他小時候如何用錄音帶作 mix-tape,如何如何、為什為什要找出獨特的 sampling...
《Scratch》的內容實在太豐富還有 Mix Master Mike、Cut Chemist、 Z-Trip、The X-Ecutioners、Afrika Bambaataa、Jazzy Jay、Gang Starr 的 DJ Premier、Rob Swift、DJ Swamp、DJ Krush、Skratchcon 2000、DMC U.S. Finals 的片段。《Scratch》實在是一部喜歡 hip hop、scratch、DJing 必看的電影/紀錄片。
延伸閱讀:Scratch official web site
www.scratchmovie.com
 在昨晚才找回失蹤多年的 Madredeus 唱片
在昨晚才找回失蹤多年的 Madredeus 唱片 一次走過外籍同事的辦公桌,他的桌上放了兩張 CD,放在上面的是 Franz Ferdinand。於是開始跟他談起音樂來,從 Franz Ferdinand 到 Coldplay、從 Keane 到 Sigur Ros 也是共同喜好。他把放在 Franz Ferdinand 下面 The Killers 的《Hot Fuss》,拿出來問我聽過沒有,我搖頭,他說《Hot Fuss》很好聽,喜歡 FF、Coldplay 的定會愛上,我就向他借來聽聽。果然 The Killers 那種青春無敵很校園味道的懷舊金曲風格,令人一聽就愛上。
一次走過外籍同事的辦公桌,他的桌上放了兩張 CD,放在上面的是 Franz Ferdinand。於是開始跟他談起音樂來,從 Franz Ferdinand 到 Coldplay、從 Keane 到 Sigur Ros 也是共同喜好。他把放在 Franz Ferdinand 下面 The Killers 的《Hot Fuss》,拿出來問我聽過沒有,我搖頭,他說《Hot Fuss》很好聽,喜歡 FF、Coldplay 的定會愛上,我就向他借來聽聽。果然 The Killers 那種青春無敵很校園味道的懷舊金曲風格,令人一聽就愛上。 經常「口出狂言」的 Brandon Flowers 其新大碟《Sam's Town》將會是"the best album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新大碟的風格也是延續《Hot Fuss》陽光燦爛青春無敵校園懷舊金曲風格。〈When You Were Young〉、〈For Reasons Unknown〉、〈Why Do I Keep Counting?〉也是一貫的清爽涼快、〈Read My Mind〉竟然大玩走音,但旋律確然優美流暢。
經常「口出狂言」的 Brandon Flowers 其新大碟《Sam's Town》將會是"the best album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新大碟的風格也是延續《Hot Fuss》陽光燦爛青春無敵校園懷舊金曲風格。〈When You Were Young〉、〈For Reasons Unknown〉、〈Why Do I Keep Counting?〉也是一貫的清爽涼快、〈Read My Mind〉竟然大玩走音,但旋律確然優美流暢。

 在家中的自選台看到 Click 的 trailer (港譯:命運自選台)。有一個片段是太太 Kate Beckinsale 在餐廳內擁抱著老公 Adam Sandler 充滿期待地問,你記得我的的「那首歌」嗎? Adam 當然是忘記了,他用那個可以把時間 fast-forward、rewind、pause 和 mute 的神奇「搖控」,把時間 rewind。原來「那首歌」就是 The Cranberries 的〈Linger〉。
在家中的自選台看到 Click 的 trailer (港譯:命運自選台)。有一個片段是太太 Kate Beckinsale 在餐廳內擁抱著老公 Adam Sandler 充滿期待地問,你記得我的的「那首歌」嗎? Adam 當然是忘記了,他用那個可以把時間 fast-forward、rewind、pause 和 mute 的神奇「搖控」,把時間 rewind。原來「那首歌」就是 The Cranberries 的〈Linger〉。 註: Who Moved My Blackberry? 是有名的《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Lucy Kellaway,被輯錄成書的其中一個專欄。 Lucy Kellaway 在這個專欄創造了一位高層 Martin Lukes,在這個專欄內用你一句我一句的 email (高層只是用 Blackberry 覆eamil),編織出很多有趣的辦公室政治、行政管理問題和 Martin Lukes 個人在事業上的高低起伏。〈Who Moved My Blackberry? 〉也被譽為〈the office 〉的文字版。
註: Who Moved My Blackberry? 是有名的《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Lucy Kellaway,被輯錄成書的其中一個專欄。 Lucy Kellaway 在這個專欄創造了一位高層 Martin Lukes,在這個專欄內用你一句我一句的 email (高層只是用 Blackberry 覆eamil),編織出很多有趣的辦公室政治、行政管理問題和 Martin Lukes 個人在事業上的高低起伏。〈Who Moved My Blackberry? 〉也被譽為〈the office 〉的文字版。
 Wyman (黃偉文)說他在年少時背 Cyndi Lauper 的 Time after Time 的歌詞,他很少女情懷地說:「就好像初戀一樣,是傻瓜的,有誰沒有曾經背歌詞...」。女朋友問我有沒有跟 Weyman 一樣背歌詞,我說:「有!當然有!喜歡聽音樂的,有誰沒有曾經背歌詞...」。
Wyman (黃偉文)說他在年少時背 Cyndi Lauper 的 Time after Time 的歌詞,他很少女情懷地說:「就好像初戀一樣,是傻瓜的,有誰沒有曾經背歌詞...」。女朋友問我有沒有跟 Weyman 一樣背歌詞,我說:「有!當然有!喜歡聽音樂的,有誰沒有曾經背歌詞...」。 一海之隔,人民在觀賞音樂和藝術表演有著天淵之別。上年澳門的國際音樂節有
一海之隔,人民在觀賞音樂和藝術表演有著天淵之別。上年澳門的國際音樂節有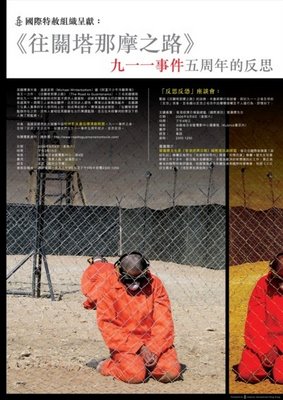




 capture from djshadow.com
capture from djshadow.com